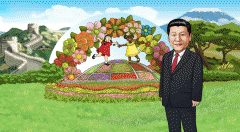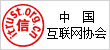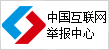|
左为张咏,右为李博 如果没有了声音,音乐还意味着什么?如果从出生开始就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歌唱又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永远会让身为“健全人”的我们长久沉默,然而就在不久前,14个从广西和厦门远道赶来的孩子在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悠远古朴的南音奏起,孩子们用一个个最简单的“啊”音节错落有致地演唱着那首专门为他们创作的《无声三部曲》。他们的声音或许并不精致,彼此的配合也算不上天衣无缝,但那种源自灵魂深处最原始、最纯粹的呐喊和轻叹,让全场观众都竖起了大拇指。 “无声合唱团”,团如其名,14个成员都是聋哑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0岁,其中,来自厦门的4个孩子不久前刚刚加入这个特殊的大家庭。无论是周围人的交谈呐喊,还是天地间的虫鸣鸟语、风雪闪电,我们习惯了的种种声响,自始至终都不曾眷顾过他们。比起身体上的异于常人,让“无声合唱团”的两位发起人李博和张咏更加牵挂的,是生活中孩子们遭遇到的有心或无意的种种伤害。“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帮孩子们建立信心”,李博说,“我们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可以感受到我们所不能感受到的东西。” 好不容易来到北京的孩子们兴奋异常,结束演出后,李博和张咏带着他们去了向往已久的长城、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凡是北京有名的景点,李博和张咏都尽量安排进行程里,让孩子们的这次北京之行不留遗憾,“明天早上我们带孩子们去看升旗,他们特别想看,所以今天晚上让他们早点儿睡了。”趁着这个机会,李博、张咏在一家咖啡馆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们有自己的世界” 李博和张咏,一个是爽朗中有点不羁的北京小伙儿,一个是身材高大、总是笑呵呵的音乐家,谁都不会想到,在合唱团演出的当晚,两个汉子还没走下台,泪水就已经溢满了眼眶。从广西的大山深处到首都北京的音乐殿堂,他们陪着合唱团走了五年才终于抵达。让自小就与声音无缘的孩子克服心理障碍开口唱歌,还要完成难度很高的合唱,背后的辛苦和酸涩,只有李博和张咏自己明白,但眼见着从前总是罩在孩子们脸上的阴霾被越来越多的微笑驱散,难以言喻的幸福总会涌上心头,“只要看到他们的表现和改变,我们觉得这几年怎么都值得了。” 时光倒流回五年前的今天,一心扑在绘画和装置里的李博可能从来都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个操心着无数琐事的称职“奶爸”。 从北京飞到南宁机场后,打车到汽车站,再坐大巴、摩托车,然后换牛车,最后步行,差不多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走进孩子们生活的、坐落在广西凌云县一个小山村里的特殊学校。2013年底,李博和张咏经过一个基金会的介绍来到这里,想把孩子们的声音做采样,用到自己的乐队音乐中。在此之前,他们刚刚被北京的一所特殊学校拒之门外,“人家不明白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想要保护孩子们,说实话也很正常。”吃了一次闭门羹,李博和张咏却没有放弃,他们深知这种鲜少被大家听到的声音到底包裹着怎样的力量与感情:某天,在热闹喧嚣的北京街头,一声“啊”的叫喊突然穿过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海,准确地击中了他们的耳朵。循着声音望过去,一位聋哑艺人正在卖力地表演,“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声音特别棒。”那种源自生命本身且未加雕饰的声音让李博和张咏为之深深震撼。 事情远比李博和张咏预期的更加困难。在特殊学校待了半个多月,仍然没有一个孩子想要接近他们,声音采样毫无进展。孩子们表现出来的状态更让他们觉得非常揪心,“不管说什么,他们都不爱搭理你。”李博和张咏一遍遍地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声音其实很棒,但自小就被“残疾”两个字深深困扰和束缚着的孩子不为所动,他们的神情总是躲闪而敏感,“可能在他们的眼里,聋哑是一种缺点,他们过不去这一关。我俩一想,算了,别在这儿折磨人了,走吧。” 正当李博和张咏在学校的走廊里准备和校长告别时,一个小姑娘的出现让一切终于有了转机。五岁的她跑到李博和张咏身边,用力地“啊”了一声,“那一声又长又稳,我俩傻眼了,一对视,决定不走了。”现在,李博非常庆幸,小姑娘薇薇的到来让当时的他们选择了坚持,“如果我们走了,还不如一开始就不来,没有这一番波澜。”在李博看来,给了美好的愿景,又不予兑现默默离开,孩子们会更加被推向“残疾”带来的极度自卑的深渊,这样造成的伤害,是我们“健全人”无从感受和估计的。 比起教会孩子们发声,摆在李博和张咏面前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怎样让他们学会更积极地看待自己。这个过程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李博和张咏想让孩子们知道,健全人眼中的所谓“残疾”,从来都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低人一等,“不能说话,不等于就没有发声的权利,听不见不等于没有感知世界的能力。” 在这所特殊学校中,还住着60多个有智力缺陷的孩子,李博有时会教他们画画,这些时常被贬斥为“智障”的孩子的作品闪耀着来自另一个神秘世界的灵光,一次又一次地让李博感到惊讶,“他们画的真的特别好,你会发现,他们是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这让李博和张咏更加相信,“聋哑”也好,“智障”也好,健全人制定的准则,不该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让这些孩子表现得像我们一样其实是不平等的,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全新的角度,这个角度不是错误的。”李博反复申明,“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方式,让所谓的健全人更加了解他们的世界。” 发声是一场修行 教孩子们发声的重任,很大一部分落在了有声乐基础的张咏肩上。尽管现在已经常居厦门,但在当年北京的音乐圈子里,张咏还是很有名气的。爵士、流行、金属、民谣、摇滚……只要是能想到的风格,他都有尝试。一般来说,各个圈子的音乐人很少互动,但张咏却在其中游走自如。后来,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张咏开始接触“南音”这门古老的艺术,而南音也是他为孩子们创作的《无声三部曲》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张咏习惯在抚琴时把头发束成发髻,换上一身飘逸长袍,他有着和外表如出一辙的隐士般的从容,遇事不慌,脸上总带着笑意,很有点儿“漫随云卷云舒”的劲头,但在孩子们身上,张咏用上了十二分的心血和努力,“他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一不注意就‘跑’了,可能飞过去个苍蝇他们都会看见,必须得一个一个盯着。”从未讲过话的孩子们舌头很软,不知道该怎么放,更没有对声音的细微感知,“记住舌头忘了呼吸,记住呼吸又忘了嗓子”。张咏和李博只能借助小球或者雪糕棍儿做成的压舌棒帮助他们知道,舌头在哪个位置发出的声音是好的。“每天都去小卖部偷人家的雪糕棍儿,我说我要买,老板不卖,那个村里别的东西又什么都没有”,无奈之下,李博后来只能每天借着去买雪糕的机会,一边交钱,一边偷偷往兜里装几根雪糕棍儿。 “我们想了各种招儿”,李博和张咏来回解释了许久,“发声对孩子们来说更像是瑜伽训练,你需要关注呼吸,关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这是一个跟自己的身体沟通的过程,声音只是结果之一,是一种副产品。”与孩子们日复一日相处下来,“语言”不通的障碍变得越发明显,为此李博和张咏不光现学了手语,还“瞎编”了一些手势,“我俩那会儿才知道,手语也是有‘方言’的,而且还很明显。” “刚开始,村里人都不太理解,校长也不理解,真的有人戳着脊梁骨说我们,你们干吗呢这是,整天跟神经病似的。家长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们只是出于对学校的信任”。坚持到了第三年,质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孩子们的训练逐渐步上正轨,张咏开始尝试着为他们独特的“歌唱”作曲,“无声合唱团”和《无声三部曲》的想法也慢慢成形。 比单纯的能够发声更让李博和张咏兴奋的,是在此过程中,孩子们的性格在一点点地改变,他们不再焦虑易怒,曾经只能在同龄的健全孩子身上看到的自信和快乐也开始浮现在他们的眉梢眼角,“合唱团不是强制的,有的孩子长大了或者因为家里的安排会离开,我们一定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我们就是希望,他们的人生中能够有这样的一段经历,有一天他们老了,还能想起这段时间,这就足够了。”
“你不想看看孩子们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吗?”2017年的秋天,忙得团团转的张咏接到了李博的电话,马上扔下手里所有的事情从厦门赶到了凌云县——孩子们成长的每一个瞬间,在他们看来都是值得见证和陪伴的。就在这一年的11月,“无声合唱团”第一次走出大山,坐上了前往厦门的飞机。游乐场、大海、灯火通明的夜市……繁华都市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美丽而生动,让孩子们止不住地欢呼雀跃。借着自己的乐队在“龙舟唱晚”音乐节上的演出契机,张咏向主办方争取到了让合唱团登台的机会。在几千名观众的注视下,孩子们的歌唱依旧有条不紊,他们如同大山里纯净的阳光和微风,曾经的怯懦阴郁完全不见了踪影。演出大获成功,回到家里后,孩子们兴奋又可爱地向同学和家人“炫耀”了好几个月。李博和张咏知道,他们完全值得更大更精彩的舞台,今年4月,通过朋友们的帮助,“无声合唱团”得到了这次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出邀请。 “越做下去,就我们两个人的力量,确实越觉得疲惫。”李博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无声合唱团”从成立的那天起,所有的开销都是他和张咏自掏腰包解决的。“有一些企业想要资助合唱团,钱我俩没敢接过,拒绝了很多,因为两个个人是说不清楚这件事的。”想要维持合唱团的运转和自己的生计,李博和张咏必须留在大城市打拼,但孩子们却需要他们更多的陪伴和了解。“之前我们每年去广西一两个月,后来就变成每年三四个月,现在只要有时间就过去。去的话还要坐最早的那班飞机,因为汽车站最后一趟车是下午两点,晚了今天可能就到不了村里。”往返奔波着实消耗了两人大量的精力。“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一个是怎么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投入,一个是怎么干干净净地把这件事做下去,这其实真的是挺难的。” 在离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候,李博和张咏就遇上了这样的麻烦。“那天是6月20日,我们跟一个基金会解了约。大家都很茫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他们更早的打算中,孩子们这次的进京表演,李博和张咏是打算和某基金会合作的。“开始大家谈的挺好,理念很一致。我俩觉得这样挺省心,以后就可以专心管合唱,外面的事儿就都交给基金会打理,也可以接受一些名正言顺的资金。”但不久后,李博和张咏就觉察到了基金会的“不靠谱儿”和想要“卖孩子”的苗头。“我们怒了,马上就跟他们断了。”李博说,“如果孩子们变成被商业用完就扔掉的人,那还不如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做这件事。” 预想中的资金突然跳票,李博和张咏措手不及,“但答应了孩子,就硬扛吧。”因为成本太高,坐飞机来北京的计划只能取消。“坐火车又要28个小时,带着这么多孩子,真是不放心,后来我们折中了一下,坐动车过来。”好心的朋友帮助李博和张咏解决了车票,还有人主动帮孩子们找到了住处,在演出时当起了孩子们的造型师。“虽然我俩是合唱团的发起人,但背后有太多人在努力,我们不能把它做砸了。它是因我们而起的,我们就负责到底。” 接下来,张咏打算再给孩子们写一些新的作品,在他看来,《无声三部曲》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健全人的审美框架,孩子们感受到的那个奇异世界只在观众面前展示了小小的一角。“现在他们还在用我们的语言来跟我们沟通,让大家先接受他们,下一步我们会尽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打破原有的和声,去把他们最原始的东西带出来。”目前,在曾经一位收藏者的建议和帮助下,李博正在准备把孩子们带往悉尼歌剧院,让更多的人聆听他们的“歌唱”。李博从没想过要给合唱团的未来设置一个明确的上限。“这几年我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过来的,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常言道“教学相长”,这些有着独特感知和理解方式的孩子们,也让李博和张咏的艺术创作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们的思路有时候太局限了,他们的范围反而更宽一些。”张咏说,“我们有太多的符号,但他们的世界里没有这些规则,就是按照最原始的状态在抒发。”五年来,李博几乎再也没有时间回到曾经的商业创作中了。大山里的日子虽然累,却有着城市里难觅的轻松和满足。“真正的艺术从来都不是要赚多少钱或者流芳百世,艺术家就像‘灵媒’,他们要负责沟通不同的世界。现在做的事,比原来我卖出作品或者在美术馆做展览更踏实。” |